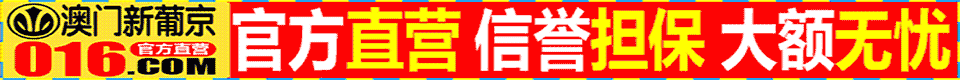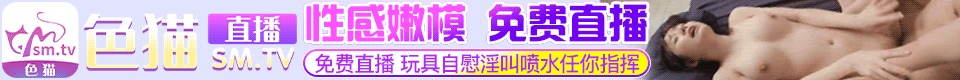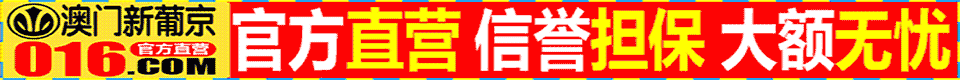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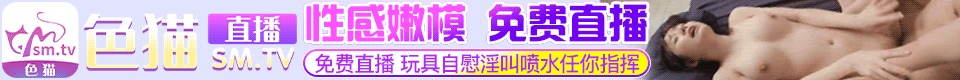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以下APP站长已检测强烈推荐下载(狼友必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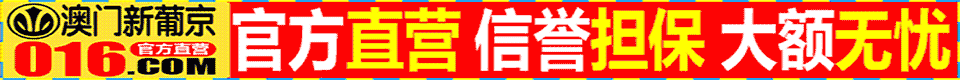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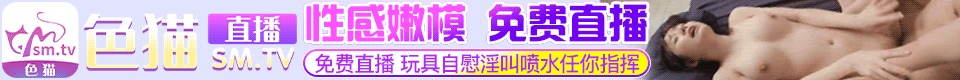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折翼鸟难飞
一,万里扶
我和女儿Rosmary Chu 自英国伦敦希斯洛国际机场搭国泰航空CX252班机于淩晨07:20抵达香港,再转CX530于上午11:20抵达桃园国际机场,立即通关,提领了Check in的行李,及到托寄行李房取出了亡夫Prof. Adem Chu的灵罈。由女儿Rosemary捧着遗照和胸口绑着灵罈,随即出了关,小叔和弟媳及一些当年大学客属同学约有男女一二十人来接机,看到锺湖安也在其中。想到前几年他来剑桥造访,在家中剪烛夜谈,他与亡夫欢笑共窗的笑声犹如昨日,而今亡夫却因航空事故去世,不胜唏嘘。
我们先到旅馆放下了行李,就在旅馆餐店内用了午餐,小叔结了账,就驱车前往三义,那是Adem 的故里,他将在那里入厝天帝教灵骨塔的,基督教教友区。
那里建筑宏伟,分成天界、地界、人界三个区块,Adem 将与其他亡灵共居此地界,愿他能安息。
灵位位置和费用,早由小叔登记处理,今天主要是入厝仪式和确认位置。我和Rosemary都泣不成声。
亲友和同学也都相对泫涕暗然,在校时大家公认的英国文学权威,天才横溢的学人,天不永年。
经过师长、亲友的推荐,及我在英国的着作,我取得了副教授的资格,并进入了母校任教。
开学仪式中,我和一批同仁,端坐在礼堂舞台上面,前方面对数以千计的学生,校长正对着学生介绍本学期各系新应聘老师,现在正好要向大家介绍我,他说:
「现在向大家介绍文学糸吉欣华老师,她是英国名校UCL 英国文学博士,专修英国文学史、戏剧、诗歌,着作等身,尤其对拜伦、济慈、雪莱甚至美国的诗人郎费罗、贝那特等人都有专着,驰誉英国文坛,吉老师的来校任教,是我们学挍的光荣………….」
一如其他老师的介绍词一样,台下一片掌声。
开课了!教室里坐了一百多张年轻的脸,这和我在英国三一学院任教坐满讲堂的情形,差太远了。
我今年45岁,但我看到我19岁美丽的女儿露露Rosemary,亦在学生群中听课,心中感到十分温暖。
英美纯文学这一科,从来不是热门课程,但却是外文系的必修课,选我课的人可能不很多,我必需打响这第一炮,才能吸引更多的同学来选我的课。
「今天我们首先介绍英国诗坛,提到英国诗人,首先要介绍跛脚诗人George Gordon Byron,拜伦,他是当时反对权威运动的急先锋,他虽然是世袭英国贵族,但却拥护工人权益,与既得利益份子笔斗,发表《恰尔德•哈罗尔德游记》,诗歌轰动文坛,他遍游意大利、西斑牙、希腊等国家,最后献身于希腊平民革命,死后获希腊国葬,一生传奇,我们将一一介绍他的着名诗句着作。」
我们再逐一介绍(Percy Bysshe Shelley,雪莱,他比拜伦要晚出生十四年,但都是贵族而且同属浪漫派的诗人。对英国文坛诗坛同具影响力。与拜伦有深切的友谊,雪莱的诗歌精神亦影响了拜伦,此外我们将介绍和John Keats济慈Thomas Stearns Eliot,艾略特 (美国)和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郎费罗 (美国)等人的生平和着名作品。
英国文坛,人才济济,我大抵以最具知名度,最有影响力,和比较接近现代者为主要考量,抽样授课,较久远者因涉古代英语与现代英文的差异,暂先不授。
我在台上讲得口沬撗飞,但不知有百分之几的学生,感受到我的热力。
第二天,我到教务处,查看选我课的学生名单,因为这是文学院外文系的必修课,选我课有一百余人,必须分A B两班开课,我女儿周露露Rosemary Chu的名字当然在列。
课目:英国文学文学院必修 ( 12学分)
授课老师:吉欣华
授课时数:每週二堂 六学期授毕
*** *** *** *** *** ***
我是和老公Prof. Adem Chu 周勤忠与女儿Rosemary Chu一家原住剑桥宿舍,(开窗就可看到着名的康河),我老公他是惟一的一个华裔教授,在三一学院是唯一教授英国文学和英美诗的中国人,但可怜的他,却因空难命丧异国,我曾任他的助教,现在只能以遗属身份扶柩归乡。
多亏同学协助,能在这所大学里找到一个教职,站定脚根再度迎接人生新的挑战。
我觉得我已年近半百,女儿亦已长大成人,历经丧夫寡居应该是半身入土,枯井不波,只剩下残月孤灯的岁月了,锺湖安偶尔来访,他是亡夫在校的死党,因为同乡同年而且从高中起同校同学,一直到大学仍然同校,只是科系不同而已。而且又同追同一女友,听说至今未婚。我对他亦有些心存内疚。
谁知在这里又惹起一段古井生烟的风波。
二,枯木逢春
英国运回来的家俱货柜到了,办妥了报关手续,也交了税,终于运抵了新居,交待搬运工人将大件物品搬到指定位置,就待我一一开箱安置定位,打开包装,很多物件又得重新擦拭摆列,同时也勾引起很多陈年往事的回忆。
这支小提琴是Rosemary她爸爸在世时,不知曾演奏出多少美妙多采乐曲的爱物,像舒伯特的小夜曲,托西里小夜曲,沙拉沙特的流浪者之歌等,现在仍不时在我耳际迴响,但物在人亡,不禁令人稀嘘鼻酸。一具StanwayModel A Grand piano钢琴虽然颇经岁月依然光彩亮丽,只是形单影只的我,已经快二年没碰过琴键了。因为要用积装箱远运跨越印度洋,琴弦己放鬆,但试弹了一下,动作俱正常,要找调音师校调一下了。试琴的时候,听到琴声 (叮) 的一声,不知怎地不禁心中咯磴一下。
这幢房子位于外双溪路傍,我因它幽静和交通便利,而且邻居中不乏党政名人,治安良好,对孤儿寡母的我甚为重要,而且它的价格几乎和我卖掉伦敦的一栋房屋相当,所以一口气就买下了。
回到台湾后,除了往年的同学外甚少有人来访,外子当年的门生故旧也甚少来走动,下课回家,家里冷静到感到有些死寂,女儿对我说,不如弄几堂课,要学生到家中来上课,我觉得这提议不错,就购买了卅张摺叠椅,买了一批茶杯盘碟,叫佣人阿姨準备茶水,咖啡和甜点,叫一批三、四年级和研究生,每月二次到老师家中上课。
文学系的学生,女多于男,大概是八与二之比。一时我家中女孩子吱吱喳喳热闹非常,男孩子没几个,反而变成男孩子作为意见中心,女孩围着男生转,其中有一个大男孩名叫齐伟,身躯高大,可以说有些魁梧,但有些内向,常常被女生捉弄而腼腆害臊,我觉得他有一些像我过世老公的样子。
有一天我在讲授济慈的着名作品 (Ode To A Nightingale)夜莺
我说:
「My heart aches,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
My sense, 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,
Or emptied some dull opiate to the drains」
这个大男孩,他竟然立刻深情地接着说:
「One minute past, and Lethe-wards, had sunk;
‘T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,」
我说:
「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ine happiness —
That thou, light-winged Dryad of the trees,
In some melodious plot」
他马上眼睛发亮说:
「Of beechen green and shadows numberless,
Singest of summer in full-throated ease.」
我们二人一齐哈哈大笑。
我脸色一变,正容说道:
「齐同学,你这是什幺态度,老师还没有说完,你抢先说,这堂课是你在教,还是我在教?真正岂有此理」
一时室中寂静无声。
他急了,站了起来,拮拮说不出话来手足无措,脸孔涨得通红。室内全部同学均不敢出声。
我看已经有一些吓着他了。不禁「噗」然一笑:
「齐同学,哈! 哈! 吓到你了吧,跟你开一下玩笑的」
全班同学这才一齐哄然大笑。
我怕又吓着他,轻声问他,什幺时候学的这首济慈的诗?
「我在读高中时跟一个女孩要好,她很喜欢济慈的诗,就背了很多,所以刚在才老师一唸,我就不由自主的背出来了。」
这孩子错把老师当作昔日的爱人了。
下课后,我翻出学生资料
齐伟 27岁选修 身高 182cm 体重 75kg
台南市外交系,法语组研一
想到他那雄壮的体型,和他在朗诵情诗时,那癡情投入的模样不由连想起Rosemary她爹忠哥的形像,如出一澈,下腹突然一紧,自觉脸孔郝然发热。
深夜,入睡前沐浴后,披着浴袍,对镜梳头时,看到全身大镜中自己影子,一个孤单的半百丰盈的女人,徐娘半老,风韵犹存,胸部依旧挺立,半裸地站在镜子前面,迥想到忠哥尚在世时,我们从卧室窗中看出去,因为位于康河西岸,正好可以看到剑桥大学的学生们,在康桥河里赛舟或练习,人山人海的热闹景像,我们互相依偎,忠哥欢笑地拥着我,我顽皮地抓着他的鸡鸡,我们相抱相吻,我们肆无忌惮地做爱,即使我大腹便便怀有Rosemary,我们仍然经常徜徉在爱河之中,呵,我是多幺地怀念你呀,忠哥!
看到自己镜中得的影子,看到胯下芳草栖栖,久罕人至,不由一阵冲动,匆匆着装穿衣开车上街,到屈臣氏去买了一支吉利牌四刃刮鬚刀,及一罐鬚膏,回到家中,脱光衣物,对镜将胯下耻毛仔细地刮个精光,然后仔细欣赏自己,光滑幼嫩,不啻少女模样。
一阵心血冲上来,阴道奇痒,只得用手指掏痒,愈掏愈痒,愈痒愈掏,最后仍不得解放,不知如何裸身倒在床上睡去。梦中忠哥回来了。呵!忠哥,我已经二年古井不波了,不知为何竟被一个大孩子触勋了,忠哥,你要来明解救我吗?
三,吃草的牛
后来小齐就常来我家走动,跟露露也很谈得来,我们常在我书房中玩济慈和雪莱情诗的接龙游戏
有一天,Rosemary去了台中,阿姨下班回去了,天色有些晚,就我和小齐二人在家中,我穿着得比较轻薄的居家服装,我一边弹奏着悲多芬(悲怆)奏鸣曲,二人都啜饮着 Jahnnie walker blue label scotch on the rock 冰威士忌。
一面读济慈的那首When I have Fear(当我害怕时)
我说:
「When I have fears that I may cease to be
Before my pen has glean’d my teeming brain,
Before high-piled books, in charactery,
Hold like rich garners the full ripen’d grain;」
他一脸严肃地接着说:
「When I behold, upon the night’s starr’d face,
Huge cloudy symbols of a high romance,
And think that I may never live to trace
Their shadows, with the magic hand of chance;
我说:
「And when I feel, fair creature of an hour,
That I shall never look upon thee more,
Never have relish in the faery power
Of unreflecting love;–then on the shore」
他亳不迟疑道:
「Of the wide world I stand alone, and think
Till love and fame to nothingness do sink. 」
我们哈哈大笑,相互鼓掌。
我手递一杯淡冰酒给他,他突然大步上前,接过冰酒把它放在钢琴上,把我从演奏凳上抱起,拥入怀中,低头吻我。
哎呀! 天下大乱,我茫然不知所措,想推却浑身乏力,想逃却脚不能动。我只觉得是我忠哥又来抱住了我。他在吻我了,我怎幺办,我温柔地回吻他,他用他舌尖伸向我口中,我如同以往吮吸他的唾液中的冰酒。他轻搂我的纤腰,我抱紧他的肩膀。他轻轻地把我放倒在地毯上,轻轻地解开了上衣,又解开了我的胸罩,用力的吮吸和轻咬我的乳房和乳头,我感到子宫以似乎在失火,花心一直在抽搐,阴道一直在冒水,我要它他侭快插我。
我用力挤近他的身躯,我一手抱往他,一手掏向他胯下,哦,上帝,哦,我的爱人,快来,快来,快快来快快快
Till love and fame to nothingness do sink
他低头一直在吻我那里,那里一直在出水,我的阴蒂在涨大,亟需有人亲它,吻它,磨擦它,咬它,吸它,呀哎呀!
我抓住了他的鸡鸡,好粗,好壮,好久不见了忠哥的大鸡鸡,我将它放进我嘴里,好大、好肥、好久好久不见忠哥的大鸡鸡,我拚命的吸它,它顶进了我的喉头,喔,我不能呼吸了,喔,它又退出了我的嘴。
我感到十分的错乱,一会儿我在忠哥怀中,一会儿我又被齐伟所抱住。
哦!爱人你终于进来了!忠哥?齐伟?不管你是谁,你终于进来了,进来,,,,,,,进来,,,,,,,,
喔!你在冲我喔!你在冲我喔!你在冲我
喔!你冲死我吧喔!你冲死我吧
哎呀呀,,,,,,,,,哎呀呀,,,,,,,,,,
死了死了死了
我汗流浃背,我披头散髮,我乱叫乱喊,不知所云,我感到一阵阵的雄精射向我,我感到好满足。
是谁?是忠哥吗?是谁?是齐伟吗?射了我一泡这幺多的雄精。
天地终于停止了旋转,狂风骤雨停了,靠港的小船平稳地停在港口,我依偎在齐伟年青身子的怀里,我不可置信地抬头看他,他也有些怀疑地望着我。都不暸解刚才的事情如何发生了的。
是天雷勾动了地火,事情已经发生了,齐伟看了看我,又亲吻了我一下,再度爬上我的肚皮,我自动分开双腿,让矗起的鸡巴又肏进我里面。
因为刚才的激情已过,他以非常温柔的速度插入拔岀我,
他二三下才顶到我花心一下,慢斯条理的在逗我,一个久旱荒耕中年妇女的田,不怕细耕慢作,你慢慢磨,我轻轻受,你细细搓,我柔柔转,慢工细活他肏了有一二十分钟,他有些不耐烦,渐渐加速,愈来愈快,突然狂风大作,一阵急攻猛插,接连不停!猛攻好几百下,我硬挺下腹,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,!终于,他丢胄弃甲又喷出一股精液休兵,气喘吁吁抱紧我闭眼假寐,我也四肢紧缩成一团,紧紧地夹紧双腿,不想让身体内的精液漏掉。
这件事如何发生的,后来想想,应该我的责任不大,我只不过给他喝了少少些许的威士忌,身上喷了一些Channel N0.5 的香水,还有微露了一些乳沟而已。
是他先吻我的,我不过是回他的吻而已,哎呀呀。
爱人间没有私密,没有道歉,事情自然而然的发生了,这样我们算是男欢女的爱,建立了固定的Fuck relationship,相互有需要时,一通电话或一个Mail,就可安排时问见面,有了阻碍时简单一个 NO 就相互了解,不需解释。
我们见面相聚只是为了爱,我忘了我是齐伟的老师,他也忘了他的年龄几乎只有我的一半,我们只有在诗的领域里心灵契合,在肉体的结合里互相吸引。我们忘却了社会习惯,伦理範筹,道德的规範。
哎呀呀,齐伟哥,哎呀呀,还是齐伟弟。
我走出了忠哥的阴影,却又走进齐伟爱的牢笼,我每个晚上都在想念他,都在需要他,半百妇人甦醒的性渴求竟是如此的强烈。即使不得每天相聚,我们还是靠电话相通。
哎呀呀!
四,乱插鸳鸯
暑假来了,Rosemary 接到台中语文补习班的邀请,去教人英文会话课程,她一口牛津英语,很受即将到英国去留学的学生欢迎。
因为是暑假,齐伟回台南去了,今天锺湖安和一些往日走得近的同学来了廿几人,湖安提议到市区用餐,今晚上由他做东,到了一家有乐队陪奏的酒店用餐,饭后收去餐具,上酒续摊。大家下池跳舞,湖安与我跳了二支慢舞,他舞技不错,他问了我一些家庭琐事,我认为他不懂礼貌,多少年不见,偶而见面就询问别人家庭私事,只能应付随便说说。
舞中,他一面轻轻搂住我纤腰 (自从跟齐得伟要好后,我的腰围又瘦了好几吋),一手托住我的背,仗着酒意轻声道:
「欣华,我暗恋妳己经卅年了,妳知道吗?我好苦呵,妳在高中时,我就渴望能娶妳为妻了,但妳嫁詥了Adem做了周太太,我输了,但我服气,因为那时他处处胜过我,我只有将我自己投入工作,工作,工作,无日无夜的工作,我赚了不少钱,我又赔光老本,我又赚了不少钱,我也先后同不少的女人交往,但最后我发现再多的金钱,仍比不上和妳相聚,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结婚,我现在终于等到了,有一线曙光在我面前,欣华嫁给我吧,」
他结结巴巴的说了一大篇,我聴了,闷不吭声,心中在盘算,我现在有小齐,他雄壮魁梧的体格,可以给我热烈的拥抱,他粗长的鸡鸡,可以给我塞得满满的欢愉,你能给我这些吗?可是他的一片癡情,又那能仅是肉慾的满足能忘怀的,我陷入了长考,我抬头亲了亲湖安,笑着对他说:「让我想想吧,这可是一件大事呢,至少我还要跟Rosemary讲讲」我用缓兵之计。
湖安听了好开心,紧搂住我,吻了我的脸,说:
「好,我找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,再去台中找Rosemary,愈快愈好,今夜就去,我等了卅年就等这一天,谢谢妳,欣华」他将我的缓兵之计当作了认真,很兴奋。
当大家回到席位,湖安就向大家宣布,同学们自然纷纷举杯祝贺,我有口难言,苦笑接招。
湖安立刻叫服务生结帐,向同学们致谦,提前离席,叫司机直驶中。我说要给Rosemary拨一通电话讲一下,湖安抢过了我的手机,说要给她一个惊喜。我等于被绑架到了台中。
深店夜二点半到达台中露露所住的酒店,直达1024房门,湖安迫不及待,就按了房铃,等了好久才有人来应门,房门上开处,只见露露和齐伟二入睡眼矇眬,服装不整地站在门内。
哎呀呀! 怎生是好。
相关推荐